中国100年抗疫的血色长歌!
1957年初夏,伟人到上海视察。
在中苏友好大厦,接见了上海医学院的教授,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苏德隆。
伟人问了苏德隆一个问题:“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?”
解放前,青浦任屯村,因血吸虫病,全村97户绝户,28户全家只活下一人。村里一户鲁姓农民,2年间摆了13张灵台。活下来的的村民,挺着像篮球一样的大肚子躺在床上,肚子上的丝丝经脉像虫子一样涌动,哀嚎冲破云霄。
在中苏友好大厦里,面对伟人的提问,苏德隆说,不能。
伟人又问,五年呢?苏德隆再答,也不能。
伟人脸色已经不对,旁边人杵了杵苏德隆。
苏德隆咬了咬牙,吐了十个字:“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”。
1958年初,苏德隆教授带着“十年消灭血吸虫病”的目标,一路南下,新中国拉开轰轰烈烈的血防战疫。
为了消灭血吸虫的宿主“钉螺”,15个乡4000名民工参与了余江县的灭螺大跃进。
第一天,4000个民工下了稻田,半数感染血吸虫病。上午灭螺,下午感染,晚上治病,第二天继续上工。
在灭螺大跃进中,将近300人因感染血吸虫病而牺牲,他们长眠在余江县的大地上,长眠在青浦的池塘边,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。
1958年夏,苏德隆带着学生在上海颛桥研究人尿灭杀血吸虫卵的效果。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,用“竹帘法”在农村的粪缸里,每天分离50公斤的疫区人口粪便。
最终得出重要的实验结论:人尿中尿素分解出的氨可以灭杀粪便中的血吸虫卵。
粪尿混合发酵,用氨阻断粪口传播,开始在全国推广。
1958-1959年,20万人口的青浦动员了150万人次参与消灭血吸虫病,湖南华容县全县一半人口参与灭螺。上万人感染,千余人牺牲。 全国一共有16000余名医护人员、药剂师、流行病学的专家,参与血防斗争。他们上山下乡,战斗在田间地头、战斗在农村旱厕中、战斗在灭螺的水田里。
参与血吸虫病防治的袁鸿昌教授,曾口述过一句话:
流行病的防治,既要有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,又要有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
这句话,贯穿了新中国抗“疫”的血色长歌。
关山虽难越,我辈屡屡越!
1
1910年,国际毛皮市场价格上升,旱獭皮价格从0.12美元,涨到0.72美元。
中国内地底层人民,出关捕杀旱獭。关外天寒地冻,捕獭人“三日粮绝即食獭肉”。
至此,鼠疫病原体,从旱獭传播至人体,并从关外大规模蔓延至内地。
哈尔滨每天死亡400余人,棺木供不应求,尸体只能就地掩埋。再后来,死了人多了,尸体直接堆在大街上。
鼠疫病原体完成了鼠传人,到人传人,到尸体传人,再到跳蚤传人的传播闭环。这场长达6个月的大鼠疫,造成6万余人死亡。
“染及一城则一城墟,染及全国则全国烬。”
中国人因欲望之贪和口腹之欲,口舌之上与舌尖之下的病毒传播,早在1910年就已经开始。
历史反复重演,但我们不长记性。
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、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,孤身携妻奔赴东北疫区,抗击鼠疫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之前,东北抵抗鼠疫靠的还是中医的针灸和推拿。中医堂里的先生们,上午给别人治病,下午自己感染,三天后暴病而亡。
一场鼠疫下来,哈尔滨的半数中医感染而死。
寻医无效之后,国人认为是天降灾难。于是,倒向了萨满教、黄巾教和跳大神的传统巫蛊崇拜中。
跳大神的大仙,经常跳着跳着,自己感染鼠疫而亡。
伍连德博士抵达哈尔滨之后,用火车车厢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隔离营;对疫区封城,关闭南满铁路、东清铁路;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医用防护口罩“双层纱布囊口罩”;严禁土葬,主张烧掉感染者尸体……
隔离、解剖、火化、烧屋消毒……满清时代的国民,面对现代医学和现代防疫措施,从一无所知,到开始畏惧和恐慌。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畏惧,并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于是,阴谋论就出来了。
伍连德作为剑桥大学的医科博士,面对普遍文盲的满清国民辱骂、质疑和泼粪,几乎无计可施,也无可辩驳。
现代医学,与传统中医、阴谋论和巫蛊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,始于1911年的哈尔滨。
乌合之众的反智主义浪潮,早在1911年就开始冲刷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
再想想现在的滴香油防肺炎、双黄连治病毒、美国基因武器、病毒泄露、实验室里的蝙蝠跑出来了……
100年过去了,似乎我们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历时4个月,这场吞噬六万条生命的清末东北大鼠疫,被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彻底扑灭。
中国人和鼠疫的战争,并未结束。
1947年5月,内蒙通辽爆发鼠疫,波及14个旗县,30306人感染,20089人死亡。通辽一县死亡过万,400余户家庭绝户。两年后,察北爆发鼠疫,波及10个村子,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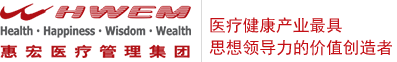

 沪公网安备 31011002000965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002000965号